《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课程授课教案(下)第八章 80年代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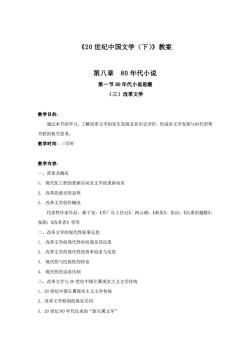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文学(下)》教案 第八章80年代小说 第一节80年代小说思潮 (三)改革文学 教学目的: 通过本节的学习,了解改革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评价,形成对文学发展与时代形势 关联的相关思考。 教学时间:三学时 教学内容 一、背景及概况 1.现代化工程的重新启动及文学的重新动员 2.改革的意识形态性 3.改革文学创作概况 代表性作家作品: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新星》、张洁:《沉重的翅膀》、 张奥:《改革者》等等 二、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反思 1.改革文学的现代性时间观及其反思 2。改革文学的现代性的效率追求与反思 3.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悖论 4.现代性的话语压制 三、改革文学与20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1.20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2.改革文学特别的现实关切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左翼文学
《20 世纪中国文学(下)》教案 第八章 80 年代小说 第一节 80 年代小说思潮 (三)改革文学 教学目的: 通过本节的学习,了解改革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评价,形成对文学发展与时代形势 关联的相关思考。 教学时间:三学时 教学内容: 一、背景及概况 1. 现代化工程的重新启动及文学的重新动员 2. 改革的意识形态性 3. 改革文学创作概况 代表性作家作品: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新星》、张洁:《沉重的翅膀》、 张碶:《改革者》等等 二、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反思 1. 改革文学的现代性时间观及其反思 2. 改革文学的现代性的效率追求与反思 3. 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悖论 4. 现代性的话语压制 三、改革文学与 20 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1.20 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2.改革文学特别的现实关切 3.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新左翼文学

敕学重点: 改革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与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密切关联。 教学难点: 改革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现代性叙事反思, 敦学手段: 课堂讲投、多媒体图像展示 思考与练习: 思考20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与时代关系。 附:讲稿
教学重点: 改革文学的时代特征及其与 20 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密切关联。 教学难点: 改革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现代性叙事反思。 教学手段: 课堂讲授、多媒体图像展示。 思考与练习: 思考 20 世纪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与时代关系。 附:讲稿

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无疑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最为宏大的主流叙事,它以明确表露的现代化渴望 承续着百年中国的历史梦幻,并以最热烈的激情和最坚定的信念传达着80年代的昂扬乐观 以及同样的平庸肤浅。因此,正如它迅速地显赫于一个时期的话语前台一样,它几乎是更为 迅速地消失于一个时代的历史叙事之中,以至于在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框架中,曾经洋洋 大观的所谓“改革文学”要么付诸阙如,'要么仅以极其少量的作品的提及而被简单化的含 混忽路。 而这一切又意味了什么呢?除了对其模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审美主义的嫌恶外,这是不 是还意味了我们思维的某种局限与懒惰?我们阐释空间的狭隘与思想资源的贫乏?抑或是 对曾经的理想热情的难以言说而无法直面?毕竟,那代表了一个梦中醒来的民族的最初的欢 欣与希望,而现实却越来越残酷地粉碎了它,日甚一日的艰苦困倾使当日的豪情万丈如今不 堪回首起来。 是的,现代化与我们血肉相连,它带给我们的欢乐与痛苦我们也只有默默承受,剥离它 如同剥离我们自己。但是,终于,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对现代化的反思正日益显示出一个新 的时代的思想深度,而这种反思的深度也同样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研究。或许,在这个时 候,我们也应该冷静地考察那激昂感奋的现代化乐章一一“改革文学”了。也许,当我们置 身当下来观察“改革文学”及80年代的时代精神文化氛围时,多重的视野纬度可以让我们 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 在80年代前期,现代化几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它以乌托邦的美好想象指引者社 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方向并激发起全体国民新一轮的乐观信念和奋斗热情,在短暂的忧郁感伤 后,现代化焕发出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现代化被作为伟大目标写进执政党的全会决议中, 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同样是以未经反思的现代化吁求作为全部讨论的基础,文学创作也 被发动起来,官方提出口号“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样,在当时主流的话语叙 如王晓明主持的“3+1工程 三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和一本《批评空间的开创一一二 十谢实 方出的百年 的秋之高华什咖年
改革文学 “改革文学”无疑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最为宏大的主流叙事,它以明确表露的现代化渴望 承续着百年中国的历史梦幻,并以最热烈的激情和最坚定的信念传达着 80 年代的昂扬乐观 以及同样的平庸肤浅。因此,正如它迅速地显赫于一个时期的话语前台一样,它几乎是更为 迅速地消失于一个时代的历史叙事之中,以至于在 20 世纪的文学史研究框架中,曾经洋洋 大观的所谓“改革文学”要么付诸阙如,1要么仅以极其少量的作品的提及而被简单化的含 混忽略。2 而这一切又意味了什么呢?除了对其模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审美主义的嫌恶外,这是不 是还意味了我们思维的某种局限与懒惰?我们阐释空间的狭隘与思想资源的贫乏?抑或是 对曾经的理想热情的难以言说而无法直面?毕竟,那代表了一个梦中醒来的民族的最初的欢 欣与希望,而现实却越来越残酷地粉碎了它,日甚一日的艰苦困顿使当日的豪情万丈如今不 堪回首起来。 是的,现代化与我们血肉相连,它带给我们的欢乐与痛苦我们也只有默默承受,剥离它 如同剥离我们自己。但是,终于,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对现代化的反思正日益显示出一个新 的时代的思想深度,而这种反思的深度也同样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研究。或许,在这个时 候,我们也应该冷静地考察那激昂感奋的现代化乐章——“改革文学”了。也许,当我们置 身当下来观察“改革文学”及 80 年代的时代精神文化氛围时,多重的视野纬度可以让我们 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 一 在 80 年代前期,现代化几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它以乌托邦的美好想象指引着社 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方向并激发起全体国民新一轮的乐观信念和奋斗热情。在短暂的忧郁感伤 后,现代化焕发出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现代化被作为伟大目标写进执政党的全会决议中, 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同样是以未经反思的现代化吁求作为全部讨论的基础,文学创作也 被发动起来,官方提出口号“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3。这样,在当时主流的话语叙 1 如王晓明主持的“3+1 工程”——三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和一本《批评空间的开创——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 2 如谢冕、孟繁华主编的多卷本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 3 本报特约评论员:《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文艺报》1980 年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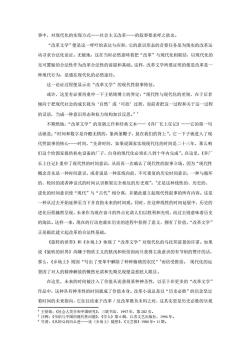
事中,对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一一社会主义改革一一的叙事要求呼之欲出。 “改革文学”便是这一呼吁的表达与应和,它的意识形态的首要任务是为现实的改革运 动寻求合法化论证。无疑地,这在当时必然意味着把“改革”与现代化相联结,以现代化的 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作为改革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这样,改革文学所要证明的便是改革是 种现代行为,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这一论证过程便显示出“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特征。 或许,这里有必要再重申一下王铭铭博士的界定:“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差别,在于后者 倾向于把现代社会的成长视为‘自然'或‘可欲'过程,而前者把这一过程和关于这一过程 的话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加以反思。”‘ 不期然地,“改革文学”的发韧之作和经典文本一一《乔厂长上任记》一一它的第一句 话就是:“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它一下子就进入了现 代性叙事的核心一时间,“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 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在这里,《乔厂 长上任记》重申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从而再一次确认了现代性的叙事立场,因为“现代性 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 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正是这种线性的、历史的、 进化的时间意识使“现代”与“古代”相分离,并循此建立起现代性叙事的所有内容。这是 一种从过去开始延伸至当下并直指未来的时间观。同时,在这种线性的时间延展中,历史的 进化历程赫然呈现,未来作为现在奋斗的终点允诺人们以胜利和光明,而过去则意味着历史 的淘汰。这样一来,现在的行动也就在历史的进程中获得了意义,拥有了价值,“改革文学" 正是据此建立起改革的合法性基础。 《旋转的世界》和《乡场上》体现了“改革文学”对现代化的乌托邦前景的许诺。如果 说《旋转的世界》尚嫌于物质主义的肤浅和世俗因而只获得主流意识的有节制的赞许的话, 那么,《乡场上》则因“写出了变革中解除了种种枷锁的农民”而倍受推崇。现代化的远 景因了对人的精神解放的概然允诺和先期兑现便益愈眩人眼目。 在这里,未来的时间被注入了价值从而获得某种神圣性,以至于在更多的“改革文学” 作品中,这种具有神圣性的时间就成了价值本身。改革小说总是以“历史必胜”的信念坚定 若时间的未来指向,它往往结束于改革/反改革胜负未料之时,这其实更是历史必胜的乐观 。行黄:《从同到3么爸读《乡场随想,《文艺报)1980年·1期
事中,对现代化的实现方式——社会主义改革——的叙事要求呼之欲出。 “改革文学”便是这一呼吁的表达与应和,它的意识形态的首要任务是为现实的改革运 动寻求合法化论证。无疑地,这在当时必然意味着把“改革”与现代化相联结,以现代化的 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作为改革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这样,改革文学所要证明的便是改革是一 种现代行为,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这一论证过程便显示出“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特征。 或许,这里有必要再重申一下王铭铭博士的界定:“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差别,在于后者 倾向于把现代社会的成长视为‘自然’或‘可欲’过程,而前者把这一过程和关于这一过程 的话语,当成一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加以反思。”4 不期然地,“改革文学”的发韧之作和经典文本——《乔厂长上任记》——它的第一句 话就是:“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它一下子就进入了现 代性叙事的核心-时间,“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 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在这里,《乔厂 长上任记》重申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从而再一次确认了现代性的叙事立场,因为“现代性 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 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5正是这种线性的、历史的、 进化的时间意识使“现代”与“古代”相分离,并循此建立起现代性叙事的所有内容。这是 一种从过去开始延伸至当下并直指未来的时间观。同时,在这种线性的时间延展中,历史的 进化历程赫然呈现,未来作为现在奋斗的终点允诺人们以胜利和光明,而过去则意味着历史 的淘汰。这样一来,现在的行动也就在历史的进程中获得了意义,拥有了价值,“改革文学” 正是据此建立起改革的合法性基础。 《旋转的世界》和《乡场上》体现了“改革文学”对现代化的乌托邦前景的许诺。如果 说《旋转的世界》尚嫌于物质主义的肤浅和世俗因而只获得主流意识的有节制的赞许的话, 那么,《乡场上》则因“写出了变革中解除了种种枷锁的农民”6而倍受推崇。 现代化的远 景因了对人的精神解放的慨然允诺和先期兑现便益愈眩人眼目。 在这里,未来的时间被注入了价值从而获得某种神圣性,以至于在更多的“改革文学” 作品中,这种具有神圣性的时间就成了价值本身。改革小说总是以“历史必胜”的信念坚定 着时间的未来指向,它往往结束于改革/反改革胜负未料之时,这其实更是历史必胜的乐观 4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和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 年,第 282 页。 5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学人》第 6 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年。 6 竹黄:《从阿Q到冯幺爸——读〈乡场上〉随想》,《文艺报》1980 年•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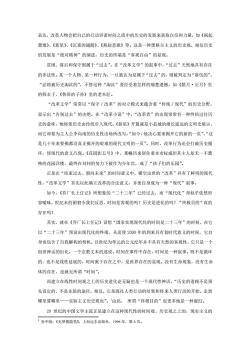
表达,改革人物会把自己的行动诉诸时间之流中的历史的发展来获取自信和力量,如《祸起 萧培》、《新星》、《沉重的翅膀》、《燕赵悲歌》等。这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观,相信历史 的发展是“绝对精神”的演进,历史的终端是“客观自由”的显现。 贫困、落后和保守则属于“过去”。在“改革文学”的叙事中,“过去”天然地具有存在 的非法性。某一个人物、某一种行为,一旦被认为是属于“过去”的,则被判定为“落伍的”、 “必将被历史淘汰的”,不管这种“淘汰”要经受着怎样的痛楚遗憾,如《腊月·正月》里 的韩玄子、《鲁班的子孙》里的老木匠。 “改革文学”常常以“保守/改革”的对立模式来蕴含着“传统/现代”的历史分野。 显示出“告别过去”的决绝。在“改革小说”中,“改革者”的出现常常有一种终结过往历 史的意味,他将使历史由传统步入现代。《新星》开篇就是小县城的漫长遥远的文明史展示, 而它却要为主人公李向南的历史性出场所改写:“如今,他决心要来揭开它的新的一页”,“这 是几十年来要揭都没真正揭开的艰难的现代文明的一页”。同时,改革行为还会打破历史循 环,使现代的意义凸现。《花园街五号》中,那幢历来居住着本市权威但其主人却无一不遭 殃的花园洋楼,最终在刘钊的努力下被作为少年宫,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正是在“结束过去、朝向未来”的时间意义中,横空出世的“改革”具有了鲜明的现代 性,“改革文学”首先以此确立改革的合法意义,并使自身成为一种“现代”叙事。 如今,《乔厂长上任记》所想象的“二十三年”已经过去,而“现代化”却似乎依然形 容暖味,世纪末的困窘令我们反思,时间是客观的吗?历史是进化的吗?“终极目的”真的 存在吗? 其实,就在《乔厂长上任记》设想“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的时候,在它 以“二十三年”预设出现代化的终端、从而使2000年的到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候,它自 身也包含了自我解构的契机。以世纪为单元的公元纪年并不具有天然的客观性,它只是一个 创世神话的衍化,一个宗教文本的述说。时间在事件中存在,时间是一种叙事。既不是循环 的,也不是线性延展的,时间寓于存在之中,是世界存在的显现。没有生命现象,没有生命 体的存在,也就无所谓“时间”。 而建立在线性时间观之上的历史进化论无疑也是一个现代性神话,“历史的道路不是预 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 哪里算哪里一实验主义历史观也”。由此,所谓“终极目的”也更多地是一种虚幻。 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正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的时间观、历史观之上的,现实主义的 7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6页
表达,改革人物会把自己的行动诉诸时间之流中的历史的发展来获取自信和力量,如《祸起 萧墙》、《新星》、《沉重的翅膀》、《燕赵悲歌》等。这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观,相信历史 的发展是“绝对精神”的演进,历史的终端是“客观自由”的显现。 贫困、落后和保守则属于“过去”。在“改革文学”的叙事中,“过去”天然地具有存在 的非法性。某一个人物、某一种行为,一旦被认为是属于“过去”的,则被判定为“落伍的”、 “必将被历史淘汰的”,不管这种“淘汰”要经受着怎样的痛楚遗憾,如《腊月·正月》里 的韩玄子、《鲁班的子孙》里的老木匠。 “改革文学”常常以“保守/改革”的对立模式来蕴含着“传统/现代”的历史分野, 显示出“告别过去”的决绝。在“改革小说”中,“改革者”的出现常常有一种终结过往历 史的意味,他将使历史由传统步入现代。《新星》开篇就是小县城的漫长遥远的文明史展示, 而它却要为主人公李向南的历史性出场所改写:“如今,他决心要来揭开它的新的一页”,“这 是几十年来要揭都没真正揭开的艰难的现代文明的一页”。同时,改革行为还会打破历史循 环,使现代的意义凸现。《花园街五号》中,那幢历来居住着本市权威但其主人却无一不遭 殃的花园洋楼,最终在刘钊的努力下被作为少年宫,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正是在“结束过去、朝向未来”的时间意义中,横空出世的“改革”具有了鲜明的现代 性,“改革文学”首先以此确立改革的合法意义,并使自身成为一种“现代”叙事。 如今,《乔厂长上任记》所想象的“二十三年”已经过去,而“现代化”却似乎依然形 容暧昧,世纪末的困窘令我们反思,时间是客观的吗?历史是进化的吗?“终极目的”真的 存在吗? 其实,就在《乔厂长上任记》设想“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的时候,在它 以“二十三年”预设出现代化的终端、从而使 2000 年的到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候,它自 身也包含了自我解构的契机。以世纪为单元的公元纪年并不具有天然的客观性,它只是一个 创世神话的衍化,一个宗教文本的述说。时间在事件中存在,时间是一种叙事。既不是循环 的,也不是线性延展的,时间寓于存在之中,是世界存在的显现。没有生命现象,没有生命 体的存在,也就无所谓“时间”。 而建立在线性时间观之上的历史进化论无疑也是一个现代性神话,“历史的道路不是预 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人类行动的结果和将来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 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7由此, 所谓“终极目的”也更多地是一种虚幻。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主流正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的时间观、历史观之上的,现实主义的 7 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第 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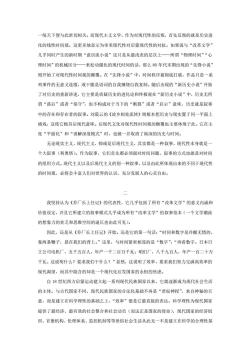
~统天下便与此密切相关。而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首先反叛的就是历史进 化的线性时间观。这更多地显示为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对抗。如果说与“改革文学” 几乎同时产生的新时期“意识流小说”还只是从最浅表的层次上一一所谓“物理时间”“心 理时间”的机械区分一一来松动僵化的现代时间的话,那么8即年代未期出现的“先锋小说” 则开始了对现代性时间观的颠覆。在“先锋小说”中,时间秩序被彻底打破,作品只是一系 列事件的无意义连缀,或干脆是语词的自我缠绕自我复制。随后出现的“新历史小说”开始 了对历史的重新讲述,它主要是质疑历史的进化论和终极观在“新历史小说”中,历史无所 谓“落后”或者“保守”,也不构成对于当下的“断裂”或者“启示”意味,历史就是叙事 中的存在和存在者的叙事。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转》则根本把历史与现实置于同一平面上 嬉戏,这使它极具后现代意味。后现代文化对现代性时间观的顺覆也主要体现于此。它在主 张“平面化”和“消解深度模式”时,也就一并取消了纵深的历史与时间。 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抑或是后现代主义,其实都是一种叙事,现代性本身就是一 个大叙事(利奥塔)。作为叙事,它们首先都必须面对时间问题,叙事的方式也就是对时间 的组织方式。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别一种叙事,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现代性 的时间观,必将会丰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充分发展人的心灵自由。 我坚持认为《乔厂长上任记》的代表性,它几乎包括了所有“改革文学”的意义内涵和 价值设定,并且它所建立的叙事模式几乎成为所有“改革文学”的叙事范本(一个文学潮流 的想象力的贫乏和思维空间的通仄也由此可见)。 因此,还是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还是它的第一句话:“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 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这里,与时间紧密相连的是“数字:“再看数字。日本日 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 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显然,这说明了效率,要求我们努力完满高效率的 现代渴望,而其中隐含的却是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的永恒的焦虑。 自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建立起一系列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它就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生活 的主体。与古代国家不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化基础不再是“君权神授”,来自神秘的天 意,而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效率”便是它最直接的表达。科学理性为现代国家 提供了最经济、最有效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而这正是国家的使命),现代国家的经济组 织、官僚机构、伦理体系、监控机制等等世俗社会生活从此无一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合理性基
一统天下便与此密切相关。而现代主义文学,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首先反叛的就是历史进 化的线性时间观。这更多地显示为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对抗。如果说与“改革文学” 几乎同时产生的新时期“意识流小说”还只是从最浅表的层次上——所谓“物理时间”“心 理时间”的机械区分——来松动僵化的现代时间的话,那么 80 年代末期出现的“先锋小说” 则开始了对现代性时间观的颠覆。在“先锋小说”中,时间秩序被彻底打破,作品只是一系 列事件的无意义连缀,或干脆是语词的自我缠绕自我复制。随后出现的“新历史小说”开始 了对历史的重新讲述,它主要是质疑历史的进化论和终极观在“新历史小说”中,历史无所 谓“落后”或者“保守”,也不构成对于当下的“断裂”或者“启示”意味,历史就是叙事 中的存在和存在者的叙事。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转》则根本把历史与现实置于同一平面上 嬉戏,这使它极具后现代意味。后现代文化对现代性时间观的颠覆也主要体现于此。它在主 张“平面化”和“消解深度模式”时,也就一并取消了纵深的历史与时间。 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抑或是后现代主义,其实都是一种叙事,现代性本身就是一 个大叙事(利奥塔)。作为叙事,它们首先都必须面对时间问题,叙事的方式也就是对时间 的组织方式。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别一种叙事,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现代性 的时间观,必将会丰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充分发展人的心灵自由。 二 我坚持认为《乔厂长上任记》的代表性,它几乎包括了所有“改革文学”的意义内涵和 价值设定,并且它所建立的叙事模式几乎成为所有“改革文学”的叙事范本(一个文学潮流 的想象力的贫乏和思维空间的逼仄也由此可见)。 因此,还是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还是它的第一句话:“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 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这里,与时间紧密相连的是“数字”:“再看数字。日本日 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 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显然,这说明了效率,要求我们努力完满高效率的 现代渴望,而其中隐含的却是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的永恒的焦虑。 自 18 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建立起一系列现代民族国家以来,它就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生活 的主体。与古代国家不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化基础不再是“君权神授”,来自神秘的天 意,而是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效率”便是它最直接的表达。科学理性为现代国家 提供了最经济、最有效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而这正是国家的使命),现代国家的经济组 织、官僚机构、伦理体系、监控机制等等世俗社会生活从此无一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合理性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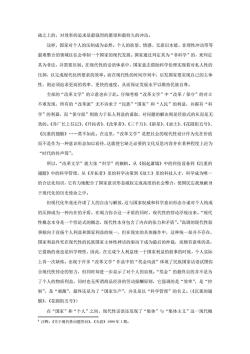
础之上的,对效率的追求是最强烈的愿望和最持久的冲动。 这样,国家对个人的压制成为必然。个人的欲望、情感、无意识本能、非理性冲动等等 最难整合的领域往往会牵制一个国家的现代发展。国家通过判定其为“非科学”的,来判定 其为非法,并需要压制。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国家意志借助科学伦理实现着对私人性的 压抑,以完成现代化所要求的效率。而在现代性的时间序列中,后发国家要实现自己的主体 性,则必须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从而保证发展水平以维持民族自尊。 全部的“改革文学”的立意也在于此。仔细考察“改革文学”中“改革/保守”的对立 不难发现,所有的“改革派”无不诉求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握有“科 学”的利器,而“保守派”则致力于私人利益的谋取,对问题的解决则是经验式的从而是无 效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改革者》、《三千万》《新星》、《故士》头、《花园街五号》、 《沉重的翅膀》.莫不如此。在这里,“改革文学”是把社会的现代性设计作为先在价值 而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加以看待,这就使它缺乏必要的文化反思内容并在某种程度上沦为 “时代的传声筒”。 所以,“改革文学”就大张“科学”的旗帜。从《祸起萧墙》中的科技设备到《沉重的 翅膀》中的科学管理,从(开拓者》里的科学决策到《故土》里的科技人才,科学成为唯 的合法化知识,它有力地配合了国家意识形态威权完成高度的社会整合,使国民忘我地献身 于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之中。 但现代化毕竟还许诺了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与国家权威和科学意识形态合谋对个人构成 的压抑成为一种内在的矛盾。在竭力弥合这一矛盾的同时,现代性的悖论浮现出来。“现代 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现代性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高调的现代性叙 事倾向于宜扬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在现实的具体操作中,这种统一却并不存在, 国家利益终究在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主体性神话的驱动下成为最后的仲裁,而颜有意味的是, 它借助的竞也是科学理性,因此,在完成个人利益统一于国家利益的叙事的时候,个人实际 上再一次缺席。出现于许多“改革文学”作品中的“奖金风波”体现了民族国家话语试图弥 合现代性悖论的努力,但同时却进一步显示了对个人的盲视。“奖金”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 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同时也无所谓商品经济的劳动报酬原则,它强调的是“效率”,是“控 制”,是“刺激”,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生产”,并且是以“科学管理”的名义。(《沉重的翅 膀》、《花园街五号》) 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现代性话语还发现了“集体”与“集体主义”这一现代概 8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避答问》,《天证》1999年1期
础之上的,对效率的追求是最强烈的愿望和最持久的冲动。 这样,国家对个人的压制成为必然。个人的欲望、情感、无意识本能、非理性冲动等等 最难整合的领域往往会牵制一个国家的现代发展。国家通过判定其为“非科学”的,来判定 其为非法,并需要压制。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国家意志借助科学伦理实现着对私人性的 压抑,以完成现代化所要求的效率。而在现代性的时间序列中,后发国家要实现自己的主体 性,则必须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从而保证发展水平以维持民族自尊。 全部的“改革文学”的立意也在于此。仔细考察“改革文学”中“改革/保守”的对立 不难发现,所有的“改革派”无不诉求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握有“科 学”的利器,而“保守派”则致力于私人利益的谋取,对问题的解决则是经验式的从而是无 效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改革者》、《三千万》、《新星》、《故土》、《花园街五号》、 《沉重的翅膀》.莫不如此。在这里,“改革文学”是把社会的现代性设计作为先在价值 而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加以看待,这就使它缺乏必要的文化反思内容并在某种程度上沦为 “时代的传声筒”。 所以,“改革文学”就大张“科学”的旗帜。从《祸起萧墙》中的科技设备到《沉重的 翅膀》中的科学管理,从《开拓者》里的科学决策到《故土》里的科技人才,科学成为唯一 的合法化知识,它有力地配合了国家意识形态威权完成高度的社会整合,使国民忘我地献身 于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之中。 但现代化毕竟还许诺了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与国家权威和科学意识形态合谋对个人构成 的压抑成为一种内在的矛盾。在竭力弥合这一矛盾的同时,现代性的悖论浮现出来。“现代 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现代性本身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8高调的现代性叙 事倾向于宣扬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在现实的具体操作中,这种统一却并不存在, 国家利益终究在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主体性神话的驱动下成为最后的仲裁,而颇有意味的是, 它借助的竟也是科学理性,因此,在完成个人利益统一于国家利益的叙事的时候,个人实际 上再一次缺席。出现于许多“改革文学”作品中的“奖金风波”体现了民族国家话语试图弥 合现代性悖论的努力,但同时却进一步显示了对个人的盲视。“奖金”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 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同时也无所谓商品经济的劳动报酬原则,它强调的是“效率”,是“控 制”,是“刺激”,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生产”,并且是以“科学管理”的名义。(《沉重的翅 膀》、《花园街五号》) 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现代性话语还发现了“集体”与“集体主义”这一现代概 8 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 年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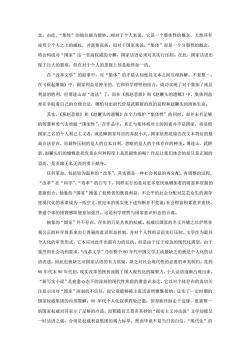
念,由此,“集体”的地位颇为微妙。相对于个人来说,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天然具有 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威权,并需要张扬:而对于国家来说,“集体”却是一个分裂性的概念, 将会构成对“国家”这一至高权威的分解,国家话语必须对其实行压制。在此,国家话语出 现了巨大的裂痕,但在对于个人的忽视上却是始终如一的。 在“改革文学”的叙事中,对“集体”的矛盾认知使其文本之间互相拆解,不复整一。 在《祸起萧培》中,国家利益是神圣的,它和科学理性相结合,成功实现了对于集体/地区 利益的胜利,但傅连山却“违法”了:而在《燕赵悲歌》和《赵镢头的遗嘱》中,集体利益 却在争取者自己的合理合法,哪怕付出的代价是武耕新的政治前程和赵镢头的肉体生命。 其实,《燕赵悲歌》和《赵镢头的遗嘱》在全力维护“集体性”的同时,却并未有足够 的智慧和勇气去质疑“国家性”。在作品中,真正与集体相对立的因素并不是国家,而是假 国家之名的个人利己主义者,或是障国家耳目的弄权小人。国家依然是隐含在文本背后的最 高合法存在,而最终压制的是人的自私自利,忽略的是人的个体存在的神圣。傅连山、武耕 新、赵镢头们的慷慨赴死究竞在何种程度上是悲刷性的呢?作品让我们体会的却只是正剧的 崇高,是英雄无私无畏的勇于献身。 任何革命,包括较为温和的“改革”,其实都是一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的过程, “改革”在“科学”、“效率”的口号下,同样实行的是对更多更快地增加者的财富和资源的 重新组合。抽象的“国家”掩盖了权势者的既得利益,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对芸芸众生的剥夺 使现代化的承诺成为一纸空文,世纪末的现实使下述判断并不荒诞:社会财富积累愈多愈快 普通个体的闲容感即便愈加强烈。这是科学理性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合谋。 抽象的“国家”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具体的权威。权威以国家的名义并辅之以俨然客 观公正的科学体系来实行普遍的意识形态控制,并对个人性的话语实行压制。文学作为最具 个人化的审美形式,它本应对此作出最有力的反抗。但是由于过于竣急的现代化渴望,由于 强烈的社会功利要求,“改革文学”乃至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主流最缺乏的就是个人化的话 语表述,因此也就缺乏对国家话语的有力质疑,缺乏对社会现代性的必要的审美制约。直到 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实改革的挫折涣散了国人现代化的凝聚力,个人话语逐渐凸现出来。 “新写实小说”是疲惫心态下的深刻的现代性焦虑的潜意识表达,它以对个体存在的真切关 注显示出对“国家”深刻的不信任,而它竞能够被主流话语所慷慨接纳,证实了一定时期的 国家权威集团的内部裂解。90年代个人化叙事四处泛滥,但却始终游走于边缘,重新整 的国家权威对其表示了足够的冷漠,而粗糙贫乏莫名其妙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却能呈 一时话语之强,分明是权威利益集团的竭力标举。然而毕竟不复当日的自信,“现代化”的
念,由此,“集体”的地位颇为微妙。相对于个人来说,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天然具有 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威权,并需要张扬;而对于国家来说,“集体”却是一个分裂性的概念, 将会构成对“国家”这一至高权威的分解,国家话语必须对其实行压制。在此,国家话语出 现了巨大的裂痕,但在对于个人的忽视上却是始终如一的。 在“改革文学”的叙事中,对“集体”的矛盾认知使其文本之间互相拆解,不复整一。 在《祸起萧墙》中,国家利益是神圣的,它和科学理性相结合,成功实现了对于集体/地区 利益的胜利,但傅连山却“违法”了;而在《燕赵悲歌》和《赵镢头的遗嘱》中,集体利益 却在争取着自己的合理合法,哪怕付出的代价是武耕新的政治前程和赵镢头的肉体生命。 其实,《燕赵悲歌》和《赵镢头的遗嘱》在全力维护“集体性”的同时,却并未有足够 的智慧和勇气去质疑“国家性”。在作品中,真正与集体相对立的因素并不是国家,而是假 国家之名的个人利己主义者,或是障国家耳目的弄权小人。国家依然是隐含在文本背后的最 高合法存在,而最终压制的是人的自私自利,忽略的是人的个体存在的神圣。傅连山、武耕 新、赵镢头们的慷慨赴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悲剧性的呢?作品让我们体会的却只是正剧的 崇高,是英雄无私无畏的勇于献身。 任何革命,包括较为温和的“改革”,其实都是一种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的过程, “改革”在“科学”、“效率”的口号下,同样实行的是对更多更快地增加着的财富和资源的 重新组合。抽象的“国家”掩盖了权势者的既得利益,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对芸芸众生的剥夺 使现代化的承诺成为一纸空文,世纪末的现实使下述判断并不荒诞:社会财富积累愈多愈快, 普通个体的困窘感即便愈加强烈。这是科学理性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合谋。 抽象的“国家”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具体的权威。权威以国家的名义并辅之以俨然客 观公正的科学体系来实行普遍的意识形态控制,并对个人性的话语实行压制。文学作为最具 个人化的审美形式,它本应对此作出最有力的反抗。但是由于过于竣急的现代化渴望,由于 强烈的社会功利要求,“改革文学”乃至整个 80 年代中国文学主流最缺乏的就是个人化的话 语表述,因此也就缺乏对国家话语的有力质疑,缺乏对社会现代性的必要的审美制约。直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现实改革的挫折涣散了国人现代化的凝聚力,个人话语逐渐凸现出来。 “新写实小说”是疲惫心态下的深刻的现代性焦虑的潜意识表达,它以对个体存在的真切关 注显示出对“国家”深刻的不信任,而它竟能够被主流话语所慷慨接纳,证实了一定时期的 国家权威集团的内部裂解。90 年代个人化叙事四处泛滥,但却始终游走于边缘,重新整一 的国家权威对其表示了足够的冷漠,而粗糙贫乏莫名其妙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却能呈 一时话语之强,分明是权威利益集团的竭力标举。然而毕竟不复当日的自信,“现代化”的

整合力在逐渐丧失,“冲击波”文学只好勉为其难地呼吁“分享艰难”,即便如此,却仍不免 招致更多的反诘与讥讽。 其实,中国的现代性叙事的根本目的就是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以此来“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这样,它就不仅通过对私人性的压制实现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同时还试图通 过对民族性的维持来独立于世界格局。于是,在这里,它就陷入了更为纠缠不清的现代性悖 论: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悖论。 在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中,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为后发国家指示了路线和方向,后发现代化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从此就只能在早发国家的影响和制约下进行,而基于发展主义之上的世界 政治经济格局在本质上的权力关系则使得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陷入窘境。一方面,它必须 加快现代化发展速度以获取民族国家真正的平等和独立:而另一方面,这一发展过程却是在 不平等格局下的对强势话语的认同过程,发展越快,认同就越强,民族国家的压抑和屈辱也 就越为深重。这是现代性的叙事逻辑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在本质上的权力关系双重作用的后 果。由此,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途也就同时背负了对现代化的渴望和对“他者化”的恐惧。 回首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吏”,还是“民族、民权、 民生”及至毛泽东时代的“赶英超美”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不是在渴望与恐惧 的困境中的勉力突围。而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官方号召下,依然有人 文知识分子在“后殖民”理论的提示下对东西方关系的高度警觉。 作为80年代前期最主流的文学话语,“改革文学”的叙事中四处流溢着一个民族国家的 现代化的渴望和焦灼,与此同时,在历史目的论的感召下,落后民族的屈辱则被当作现代化 必须支付的代价掩饰进国人的无意识底层,民族主义的情绪受到抑制。但是,毕竟与现代性 密切相关,毕竟触及主权国的最敏感神经,关乎民族意识的话语还是从叙事的缝隙中流溢了 出来,在互相矛盾互相拆解的片断表述中,民族主义的话语闪烁迷离,传达出“第三世界文 化中的寓言性质”(杰姆逊)。 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一个日本人无意的抬举令乔光朴“脸躁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擦 出了水”,民族的屈辱赫然浮现。但这种屈辱却并未导向为民族主义的敌视和排斥,而是反 转过来,指向自身:“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由此,现代化的渴望转移了民族主义 的焦虑,使其转化为自我奋斗的动力:而这种自我奋斗的过程其实正是一个向他民族认同的 过程。现代性叙事的逻辑转换回避了民族国家间实质上的权力关系,掩盖了经济强势下的政
整合力在逐渐丧失,“冲击波”文学只好勉为其难地呼吁“分享艰难”,即便如此,却仍不免 招致更多的反诘与讥讽。 三 其实,中国的现代性叙事的根本目的就是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以此来“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这样,它就不仅通过对私人性的压制实现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同时还试图通 过对民族性的维持来独立于世界格局。于是,在这里,它就陷入了更为纠缠不清的现代性悖 论: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悖论。 在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中,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为后发国家指示了路线和方向,后发现代化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从此就只能在早发国家的影响和制约下进行,而基于发展主义之上的世界 政治经济格局在本质上的权力关系则使得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陷入窘境。一方面,它必须 加快现代化发展速度以获取民族国家真正的平等和独立;而另一方面,这一发展过程却是在 不平等格局下的对强势话语的认同过程,发展越快,认同就越强,民族国家的压抑和屈辱也 就越为深重。这是现代性的叙事逻辑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在本质上的权力关系双重作用的后 果。由此,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途也就同时背负了对现代化的渴望和对“他者化”的恐惧。 回首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民族、民权、 民生”及至毛泽东时代的“赶英超美”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不是在渴望与恐惧 的困境中的勉力突围。而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官方号召下,依然有人 文知识分子在“后殖民”理论的提示下对东西方关系的高度警觉。 作为 80 年代前期最主流的文学话语,“改革文学”的叙事中四处流溢着一个民族国家的 现代化的渴望和焦灼,与此同时,在历史目的论的感召下,落后民族的屈辱则被当作现代化 必须支付的代价掩饰进国人的无意识底层,民族主义的情绪受到抑制。但是,毕竟与现代性 密切相关,毕竟触及主权国的最敏感神经,关乎民族意识的话语还是从叙事的缝隙中流溢了 出来,在互相矛盾互相拆解的片断表述中,民族主义的话语闪烁迷离,传达出“第三世界文 化中的寓言性质”(杰姆逊)。 在《乔厂长上任记》中,一个日本人无意的抬举令乔光朴“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 出了水”,民族的屈辱赫然浮现。但这种屈辱却并未导向为民族主义的敌视和排斥,而是反 转过来,指向自身:“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由此,现代化的渴望转移了民族主义 的焦虑,使其转化为自我奋斗的动力;而这种自我奋斗的过程其实正是一个向他民族认同的 过程。现代性叙事的逻辑转换回避了民族国家间实质上的权力关系,掩盖了经济强势下的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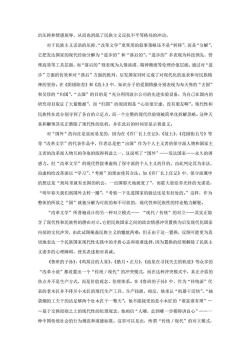
治压抑和情感屈辱,从而也消泯了民族主义反抗不平等格局的冲动。 对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压抑,“改革文学”更常用的叙事策略还不是“转移”,而是“分解”, 它把发达国家的现代经验分解为“进步的”和“落后的”:“进步的”多表现为科技领先、管 理高效等工具层面,而“落后的”则表现为人情淡漠、精神颓废等伦理价值层面。通过对“进 步”方面的仿效和对“落后”方面的批判,后发国家同时完成了对现代化的追求和对民族精 神的坚持。在《阴错阳差》和《故土》中,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分别表现为布天隽的“去国” 和吴珍的“归国”,“去国”的目的是“充分利用波尔公司的先进实验设备,为自己在国内的 研究项目取证了大量数据”,而“归国”的原因则是“心里很空虚,没有朋友啊”。现代性和 民族性在此分别寻到了各自的立足点,而一个完整的现代经验则被简单化拆解忽略。这种天 真和颛预其实正潜隐了现代性的危机,并在此后的时间里显示着意义。 对“国外”的向往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乔厂长上任记》、《故土》、《花园街五号》等 等“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中,作者总是把“出国”作为个人主义者的保守派人物和国家主 义者的改革派人物互相争取的既得利益之一,这说明了“国外”一—发达国家一一永久的诱 惑力。但“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虚构了保守派的个人主义的目的,由此判定其为非法, 而虚构给改革派以“学习”、“考察”的理由使其合法。如《乔厂长上任记》中,保守派冀申 的想法是“到局里就有出国的机会,一出国那天地就宽了”,而霍大道给乔光朴的允诺是, “明年春天我们到国外去转一圈”,“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做法还是有好处的。”这样,作为 整体的所欲之“国”就被分解为可欲的和不可欲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悖论勉力解脱。 “改革文学”所普遍设计的另一种对立模式一一“现代/传统”的对立一一其实正隐 含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潜在对立。它把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情感冲突置换为后发现代化国家 内部的文化冲突,由此试图掩盖民族主义的尴尬两难:但正由于这一置换,反倒可能更为真 切地表达一个民族国家现代性实践中的矛盾心态和艰难选择,因为置换的结果解除了民族主 义诸多的心理障碍,使其表述相对真诚。 《鲁班的子孙》、《鸡窝洼的人家》、《脂月·正月》、《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等众多的 “改革小说”都设置出一个“传统/现代”的冲突模式,而在这种冲突模式中,真正矛盾的 焦点并不是生产方式,而是价值观念、伦理体系。在《鲁班的子孙》中,作为“传统派”代 表的老木匠并不排斥小木匠的现代生产工具、生产技能,相反,他承认“机器干活快”,“抽 袋烟的工夫干的活足够两个壮木匠干一整天”:他不能接受的是小木匠的“谁富谁有理” 一基于交换原则之上的现代性的伦理观念,他相信“人哪,走到哪一步都得讲良心” 种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这里可以见出,所谓“传统/现代”的对立模式
治压抑和情感屈辱,从而也消泯了民族主义反抗不平等格局的冲动。 对于民族主义话语的压抑,“改革文学”更常用的叙事策略还不是“转移”,而是“分解”, 它把发达国家的现代经验分解为“进步的”和“落后的”;“进步的”多表现为科技领先、管 理高效等工具层面,而“落后的”则表现为人情淡漠、精神颓废等伦理价值层面。通过对“进 步”方面的仿效和对“落后”方面的批判,后发国家同时完成了对现代化的追求和对民族精 神的坚持。在《阴错阳差》和《故土》中,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分别表现为布天隽的“去国” 和吴珍的“归国”,“去国”的目的是“充分利用波尔公司的先进实验设备,为自己在国内的 研究项目取证了大量数据”,而“归国”的原因则是“心里很空虚,没有朋友啊”。现代性和 民族性在此分别寻到了各自的立足点,而一个完整的现代经验则被简单化拆解忽略。这种天 真和颟顸其实正潜隐了现代性的危机,并在此后的时间里显示着意义。 对“国外”的向往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乔厂长上任记》、《故土》、《花园街五号》等 等“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中,作者总是把“出国”作为个人主义者的保守派人物和国家主 义者的改革派人物互相争取的既得利益之一,这说明了“国外”——发达国家——永久的诱 惑力。但“改革文学”的现代性叙事虚构了保守派的个人主义的目的,由此判定其为非法, 而虚构给改革派以“学习”、“考察”的理由使其合法。如《乔厂长上任记》中,保守派冀申 的想法是“到局里就有出国的机会,一出国那天地就宽了”,而霍大道给乔光朴的允诺是, “明年春天我们到国外去转一圈”,“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做法还是有好处的。”这样,作为 整体的所欲之“国”就被分解为可欲的和不可欲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悖论勉力解脱。 “改革文学”所普遍设计的另一种对立模式—— “现代/传统”的对立——其实正隐 含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潜在对立。它把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情感冲突置换为后发现代化国家 内部的文化冲突,由此试图掩盖民族主义的尴尬两难;但正由于这一置换,反倒可能更为真 切地表达一个民族国家现代性实践中的矛盾心态和艰难选择,因为置换的结果解除了民族主 义诸多的心理障碍,使其表述相对真诚。 《鲁班的子孙》、《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等众多的 “改革小说”都设置出一个“传统/现代”的冲突模式,而在这种冲突模式中,真正矛盾的 焦点并不是生产方式,而是价值观念、伦理体系。在《鲁班的子孙》中,作为“传统派”代 表的老木匠并不排斥小木匠的现代生产工具、生产技能,相反,他承认“机器干活快”,“抽 袋烟的工夫干的活足够两个壮木匠干一整天”;他不能接受的是小木匠的“谁富谁有理”— —基于交换原则之上的现代性的伦理观念,他相信“人哪,走到哪一步都得讲良心”——一 种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这里可以见出,所谓“传统/现代”的对立模式
按次数下载不扣除下载券;
注册用户24小时内重复下载只扣除一次;
顺序:VIP每日次数-->可用次数-->下载券;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课程教学大纲(下).doc
- 安徽大学:《比较文学》课程授课教案(讲义,共八章).pdf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鲁迅与《呐喊》和《彷徨》.ppt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鲁迅与《呐喊》和《彷徨》对鲁迅的评价.ppt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诗经》与中国诗歌的起源.ppt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老、庄与道家文化_老庄.ppt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四章 向往自由_贝多芬.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四章 向往自由_爱因斯坦说.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四章 向往自由_爱因斯坦的一生.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四章 向往自由_《贝多芬传》译者序.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第四章 向往自由.pptx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十章 坚忍的山峦_负载着理想的荒凉.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十章 坚忍的山峦_精神康复之路的探寻.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十章 坚忍的山峦_王家新的人物诗——读诗集《王家新的诗》[桑克].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十章 坚忍的山峦_爱的审判——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十章 坚忍的山峦_承担者的诗:俄苏诗歌的启示 - 思与文.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十章 坚忍的山峦_安兆俊.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十章 坚忍的山峦_女性散文12家之筱敏:雕塑里有声音.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十章 坚忍的山峦_写散文就要有自由的精神.doc
-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课件(参考材料)第十章 坚忍的山峦_个人对历史的承担.doc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课程教学单元(上)第二章 鲁迅.pdf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课程教学单元(上)第五章 二十年代的诗歌.pdf
- 《汉语写作》课程教学大纲.doc
- 《汉语写作》研究性课程教学方案.doc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大纲 Intermediate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一).doc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大纲 Intermediate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二).doc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大纲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人培).doc
- 石河子大学:《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授课教案(上册).doc
- 石河子大学:《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授课教案(下册).doc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资源(讲稿,上册).doc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资源(讲稿,下册).doc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第一课 让我们认识一下.ppt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第四课 有什么别有病.ppt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第三课 民以食为天.ppt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第二课 购物,让我欢喜让我忧.ppt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第六课 就业的路有多长.ppt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第五课 爱情是什么.ppt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第七课 悠着点,别累着.ppt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第八课 善待你的钱包.ppt
- 《大学汉语听说》课程教学课件(PPT讲稿,下)第五课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ppt
